屋后的那片菜园……
来源:今印江新闻客户端
发布时间:2025-08-28 17:58
浏览量:11707
立秋刚过,屋后那片承载着无数回忆的菜园,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灿烂的季节。鲜红的辣椒如同一串串燃烧的小灯笼,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泽;紫色的茄子宛如一个个优雅的精灵,静静地挂在枝头;黄色的南瓜圆润饱满,像一个个金色的太阳;细长的豇豆,自以为是身材姣好,在风中摇曳生姿;努力朝着枝头攀爬的葫芦,高调地随风招摇;而懒洋洋趴在篱笆上的丝瓜、番茄、芬芳馥郁的生姜、躲在角落里的阳荷和小葱,虽低调,却也散发着独特的芬芳。这片菜园,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,意义远不止于那片充满生机的绿色。在老家,有着“菜当三分粮”的说法。那时,哪家要是有个红白事务,送的礼大多是粮食,少则十斤,多则两箩筐。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,粮食成为了人情往来的重要纽带。因此,要让全家不饿肚子,菜园就成为了必须精心“深耕”的责任地。回忆起小时候,寨子里的人总是喊我们“搬家客”,态度里还带着几分不和谐,而且我们家的田地比别家人要窄许多,所以,小小的菜园我们种得格外仔细些。我心中一直充满疑惑,每当问起父亲为什么乡亲们要喊我们“搬家客”,他总是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们好好努力,争取长大后再做一次‘搬家客’。”那时的我,对父亲的话百思不得其解,但屋后那片菜园却成了我童年最大的慰藉。 每当冬雪完全融化,父亲便成了这块菜园的“总设计师”,他坐在有些磨得光滑的石头上,左手扶着烟斗,右手的食指不停地指挥着:“黄瓜栽在最外边,他们几个一天打百、八十遍,不把我其他的菜踩坏了;茄子只种两行,炒起来费油;辣椒多种点,一年四季都可以吃;丝瓜、番茄顺着篱笆种;南瓜、豇豆靠土坎边;葫芦种在桃树下,还免了搭瓜棚……”父亲总是按照他的意愿,把菜园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当然,他心里也怀揣着一点小私心,因为他喜欢吃辣,所以每年都会安排把辣椒种得多一些。 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,则成了父亲计划的忠实执行者。冰雪融化后,菜园的土会变得蓬松些,我们便脱掉棉袄,拎着锄头、铁锹开始整土。虽然整土的过程有几分费力,但其中却乐趣无穷,惊扰了冬眠的蚯蚓,翻出爱扎推的蚂蚁,还挖出“花了心”的萝卜,这些小小的发现都让我们兴奋不已。 一声春雷,像是劳动的集结号。母亲便把辣椒、茄子、黄瓜等菜的秧苗育上。约莫二十多天,各种秧苗就粗壮地破土而出了。母亲在忙完其他的农活后,总会抽点时间来把菜种上。我们放学后,也会加入种菜的队伍。母亲总说,种菜是有技巧的,要选好的天气,天上不晒,地上不湿,这样既能保证土地的蓬松,又让秧苗不被晒着,成活率就高。所以我们家的菜园里,很多活计都是在提着煤油灯的夜晚完成的。昏暗的灯光下,影子拉得悠长,一家人忙碌的身影,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。 随着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,浇水、施肥、捉虫、除草,这些活计一点也不落下,菜园里的菜也长得郁郁葱葱。比巴掌还大的黄瓜叶下,一根根带着小刺和花朵的黄瓜悄然爬满瓜蔓;背面带刺叶子下,紫色的茄子也如拇指大小,丝瓜、南瓜也竞相开花,绿叶下,不经意间也藏着一个个小瓜,让人满心期待。最幸福的时刻,是黄瓜褪去“青涩”,变得镰刀把大小,约莫十多公分长,便成了我们口中既是食物又是水果的美食,也成了童年甜甜的回忆。最美的时刻要数番茄红时,一串串成熟的小番茄,像瀑布似的倾泻在篱笆上,红得惊艳。顺手摘下一颗,泥土的芬芳和着番茄的酸甜,是夏天最好的解暑方式;也可以摘下几颗,用猪油爆香之后,加上一瓢山泉水,煮上一碗自家采制的面条,填满了饥肠辘辘的肚子,也填满幸福美满的童年。顺着时令,各种蔬菜也呈现在餐桌上,丰富着全家的味蕾,填饱着全家的肚子,窄窄的菜园俨然变成一个“小粮仓”。 一年四季,春去冬来,这片菜园,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辛勤付出与团结协作。父亲用他的智慧和经验规划着菜园的布局,母亲用她的勤劳和细心呵护着每一株秧苗,而我们姐弟三人则在劳动中学会了责任与担当。在不断地耕种中,也逐渐明白了父亲意味深长的话语。因为我们常年居住的地方,隔外婆家很近,却隔奶奶家很远。如今,时光流转,那片菜园的“总设计师”已去了另一个世界,耕种者已仅剩母亲,但屋后那片菜园依然郁郁葱葱,虽然没有了当年的热闹与忙碌,但每一次回到老家,看到那片熟悉的菜园,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长大后的我们,按照父亲的愿景,又真的再一次成了“搬家客”,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搬走……(张玉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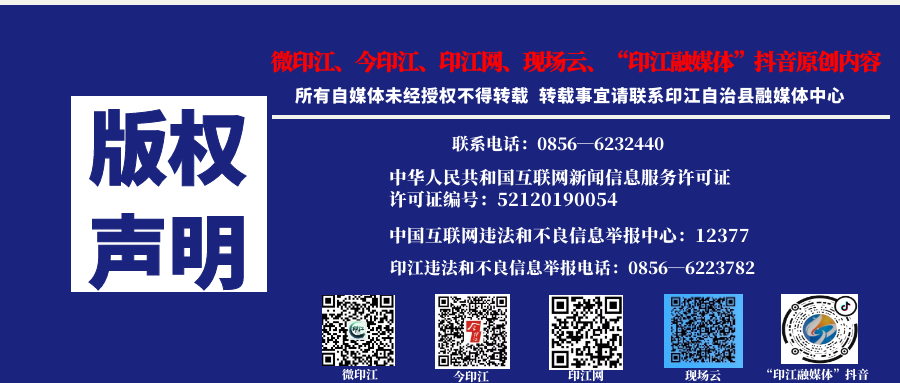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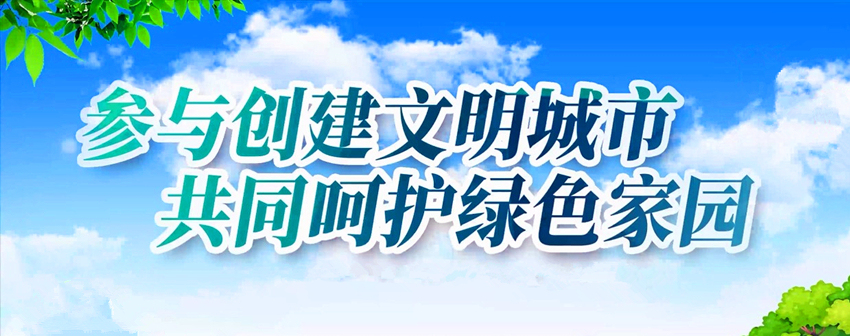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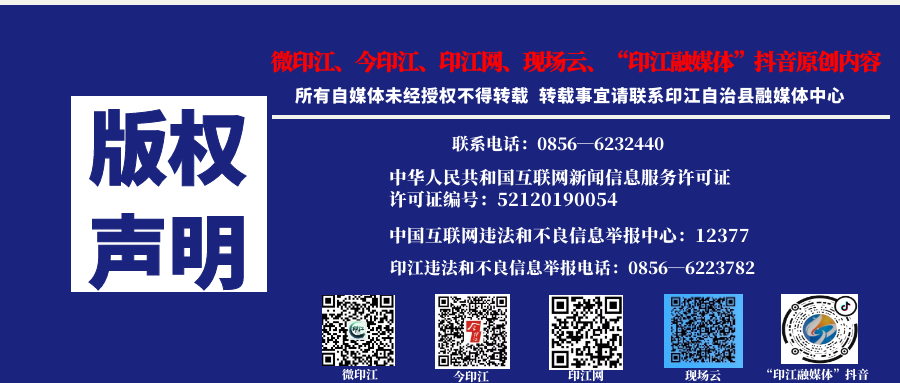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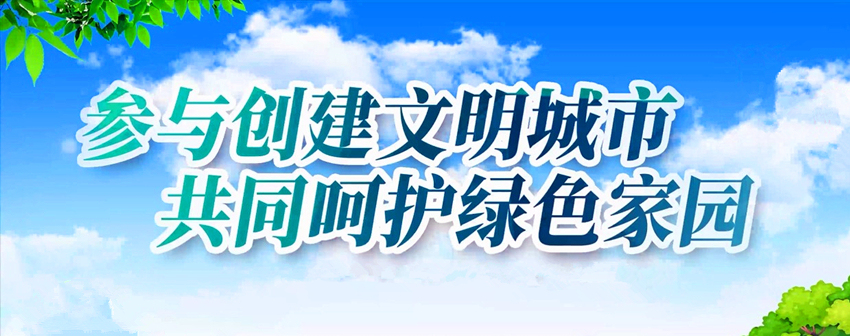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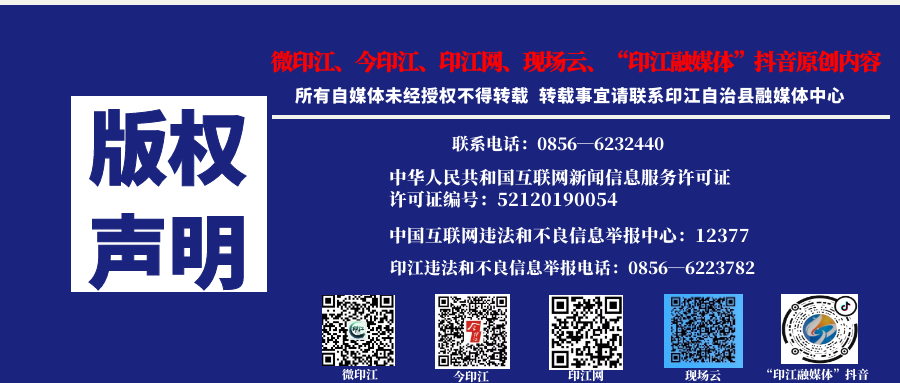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田林 编辑:王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