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江印象·文脉印江 | 事物都有尽头,唯独思念没有
来源:今印江新闻客户端
发布时间:2025-04-10 18:13
浏览量:1199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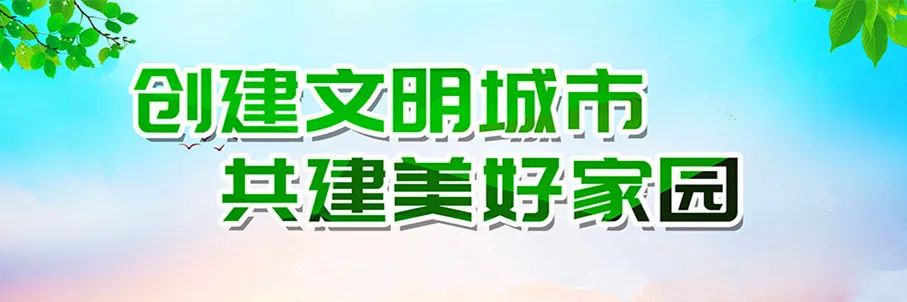
刚进入秋天,下了场雨,早晚的天气就特别凉爽了。炎热的夏季像是被逼退在某个角落,积蓄着力量,随时准备复出。高温在大中午准会冒出来,一直持续到下午,晚上又特别凉爽,甚至有点冷。外公比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秋天的天气变化。一天中什么时候最冷、什么时候最热,什么时候不冷不热,天气像酒精一样顺着他脸上、手上、脚上的皮肤进入身体,冷热分明。
外公在床上躺了大半年,中途有几天他能走一点路。早上,儿孙们都起床后,在屋檐下坐着聊天。舅舅扶外公到院坝走走。大家用欣喜的眼光看着外公摇摇晃晃地走着。外公不要舅舅扶,他佝偻着身子,拄着木棍,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迈步。舅舅不放心,在后面跟着。
初夏的晨光就着一缕缕山风穿过晨雾,从屋后照过来,照在院边茂盛的、湿漉漉的南瓜叶上,满眼的绿色鲜亮而蓬勃。几朵金黄的南瓜花点缀其间,喇叭口有蜜蜂飞进飞出。扒开南瓜叶,拳头大小的南瓜毛茸茸的,与水泥地接触的地方湿了一小块,像极了在尿床上贪睡的孩子。一根南瓜藤悄悄地试探着,往院坝中央爬。一半阴凉一半明亮的院坝里,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及阳光下黑黑的影子,小心翼翼地缓慢移动。外公突然转过头,吼舅舅,你不要跟着我。舅舅只好站在原地。外公用了三十多分钟,蹒跚着在两百平米的院坝里走了一圈,从出发的起点又回到起点。外公学走路的场景让人欣喜,更让人悲伤。外公走这一圈多像一个隐喻:在人生这条路上,他用了七十六年的时间,从学走路又回到学走路。

我本想表扬一下外公。外公真棒!外公好厉害!这样的句子确实说不出口。外公从我热烈的掌声里,感受到我的喜悦,就像他几十年前看着舅舅姨妈们学会走路时的心情一样。他要坚持再走一圈,这是他躺床上六个多月来第一次下地走路。最高兴的应该是外公自己。病倒之前,外公的双脚就没有离开过泥土,从早走到晚,从春走到冬,不停地走。年轻时,每天天不亮,家里就有他和外婆的脚步声,他挑着空水桶出门的脚步声轻盈而敏捷,挑着一担水回家的脚步声稳重而坚实。水缸里的水满了,明晃晃的,外公年轻的脸被一缸晃荡的清水映照得歪歪斜斜。那会儿,他还要每天挑着粪桶走到土里,从土里挑着土豆、玉米回家。外公坚信,种庄稼只有不停地挑出去,才会不停地挑回来。外公背后的十三张嘴巴像十三根鞭子,时刻抽打着外公的双腿,他只有不停地走,不停地劳作,家里的九个儿女和两个母亲才不会饿肚子。
那时外公肩上总是挑扛着重重的粪桶或粮食,也扛着生活的巨大负担,他依然健步如飞。可现在,什么都不用挑了,外公每走一步却无比艰难和费劲。其实,半边身子瘫痪的外公走一圈已经很累了,他的左腿像灌了铅一样重,只能让右腿拖着走。他之所以要坚持走两圈,他希望左腿突然灵活起来,像以前那样,和右腿一起支撑起身体,走到土里去,走到田里去、走到山林里去。即使什么都拿不动,闻闻泥土的气息、野草的涩味,看看庄稼在微风中波浪般起伏,抱抱那棵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树,多好呀!才走完一圈半,外公纤细的右腿已经拖不动左腿了。他弓着身子,右手紧紧地握着木棍,身子有些摇晃。舅舅跑过去扶他,“给我滚开了”五个字从他的喉咙里滚出来,铿锵中带着愤怒,就连在院坝边啄食的母鸡都被吓跑了。好几次,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挪动左腿。最后只能绝望地坐在舅舅为他搬来的椅子上。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,鼓励他,他都一言不发。
外公每天都坚持在院坝里走走,每天都有一点进步。天气好的话,早上走两圈,天黑前也要走两圈。九个儿女要养家糊口,有各自的事情要做,看到外公一天天好起来,都相继离开。每天排队打电话问他走了几圈,吃了多少饭,外公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。
外婆不在家的时候,外公就在房间里走走。支撑身体的拐杖,每走一步,重重地杵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咚咚的声音间隔时间较长,却不间断。外公甚至能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倔强的外公坚信,他一定能自如地走出房门,走到田野山林去。
过了半个月,我们都以为外公可以走很多圈了,可外婆却在电话里生气地说,一步都不能走了。他趁外婆不在家,到另外一个房间偷喝了外婆用于按摩脚踝的药酒。胃溃疡和肺气肿又犯了,进不了食,只能躺床上。在外打工的九个儿女从四面八方赶回来,白天夜晚的守着他。病痛折磨着外公,除了不停地呻吟,他躺着也懒得动一下。偶尔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只要九个儿女有一个不在床前,外公就用尽全身力气踢被子,喘气也急促。大家都以为外公熬不过那几天,悄悄且慌张地准备后事所需的物品。
外公突然说他要去医院,说他的病在医院打吊针就能好。却没人敢送他去医院,大家都怕他死在去医院的颠簸中,老家离县城医院一个多小时车程。大家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,不希望这一个多小时车程成为他和儿女们永远的距离。外公又开始踢被子,狂躁不安,挣扎着起床,说大家不送他去医院,他自己走路去,他养了一群白眼狼。最后,是急救车来接去的。医生的话让大家感到特别意外,说外公身上的器官开始衰竭,右脑萎缩。在医院的第一天,外公安安静静的接受检查和打吊针。第二天,趁舅舅不注意,他把吊针的针头取下来放在自己的耳朵里。他说他要回家,他不能死在医院,他怕被火化。
在县医院只呆了三天就回家,这三天的效果是神奇的。回到家后外公虽然只能躺着,但精神了很多,也能喝小半碗米粥。见外公一天天好转,儿女们又相继离开了。家里只留下外婆、大舅和小舅照顾他。大舅小舅每天依然要下地劳作,只能晚上陪他,照顾外公的重担就落在外婆肩上。
白天,偶尔有寨子里的人去看望外公,陪他说说话,没人的时候他也能平静地躺一会儿。夜晚,特别是大家都睡去了,病痛中的外公只能一分一秒的熬着。人们一觉睡到天亮还嫌睡不够的几个小时,对于外公来说就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,长得没有边际。外公只有不停地喊,一会儿要喝水,一会儿要小便,一会儿要吃药。外婆起床慢了,就要被他骂,骂完外婆骂舅舅,骂完舅舅骂姨妈!摔右手边能摸着的东西,实在没东西摔,用手拍木板壁。大舅舅小舅舅不来他床前也骂,到床边照顾他更骂。其实,属于外公的时间越来越少,外公已经陷入了时间的深井里,他觉得时间就像他的病痛一样没有尽头。
周末,我和爱人去看望外公,外公见着我们就说,你们忙就不要来看我了。但我知道他是多么希望我们去看他。外公的床在窗子下面。他背靠着木板壁,斜躺在床上,双脚放在床边的凳子上。左脚肿胀得黑乎乎的,除了脚板,看不见一点好肉。外婆说是之前按摩排乌血的伤口被感染了,每天擦点碘酒。右脚和双手都只剩下皮包着骨头,青筋突兀。七月的一束阳关从窗外照进来,常年被烟熏的木板房显得更幽暗了,瘦得像纸片的外公躺在幽暗的角落里,好一会儿才看清外公干枯的脸。没聊几句,外公有气无力地向我抱怨起他的九个儿女来。
那会儿养他们九个,吃树皮野菜也没现在这么难过。他们只要一生病就背着去找医生,爬坡上坎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医院。可我现在病了,没人管。前几天全都在这里,满房间都是,这几天一个人影也见不着。辛辛苦苦把他们九个养大,平时没要他们管,就是希望在我生病的时候能靠着他们。突然话锋一转,你爸爸也好几天没来看我了,只是昨晚打了个电话。我就这样听外公唠叨,等他唠差不多了,劝他,有事要好好和舅舅说,不能骂他们,你骂他们,他们就不敢进你的房间了。听我这么说,外公又把刚才说的话不紧不慢地又重复了一遍。
外公叫我出去叫外婆,他要小便。我趁此机会出去透透气。尽管外婆每天都要拖地,给外公擦身子,房间里尿味、药味及老人身体特有的味道混合着,让人喘不过气。
外婆正在炒菜,说你忍一下,炒菜放不得手。我接过锅铲,外婆进屋去,外公已尿床上了,外婆又要忙着给他换裤子和床单。外婆侍弄好外公,从房间出来,也开始抱怨起外公来。说外公不听话,老大不小了,一不顺心就骂,说要大小便一秒钟也等不了。外婆七十七岁的人了,自己都需要人照顾,却不得不这样照顾外公。
外婆说,外公身上的器官都不好了,只有嘴巴还是好的,骂大家骂得难听。
记忆中,年轻时的外公温和而儒雅。外公喜欢打算盘,他经常翻来大集体年代的账本,发黄的账本上面全是蚂蚁般密密麻麻的数字。外公右手不停地拨算盘珠子,左手食指不时伸到舌头上沾点口水,从账本的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。外公拨算盘的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感,像是弹一首好听的曲子。拨到最后,外公总会满意地一笑。记得外婆说过,当时大队有人搞外公名堂,说他把分配的粮食算错了。他就一遍一遍打算盘,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证明自己没算错,就这样养成没事打算盘的习惯。外公还会拉二胡,小小的我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,只是觉得声音有时轻快跳跃,有时浑厚圆润,有时平和柔美,听着特别悦耳。外公拉二胡的声音一响,院坝里准能吸引一圈人,有抱着小孩听的,有端着饭碗听的,有抽着旱烟听的,也有做着针线活听的。因为家里人口多,外公还学会看简单的病,家里的柜子上全是大小不一、高矮不等的棕色瓶瓶罐罐,装着白色的药粒。有人来买药,外公就用一把闪着银光的小勺子从罐子里耐心地舀出一片片药粒。
现在,外公病得只剩下骂人的力气。一个多月后,外公的嘴巴也不大好了,有时问一句答一句,有时问几句都不答一句。外公终日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,任凭病痛折磨,以数房间的木板来熬日子。房间里的木板一会清晰、一会儿模糊。外公连一间小房子的木板都数不清楚了,更不用说他年轻时修建的四栋大木房的木板,那些不计其数的木板只能用算盘才能计算清楚,全是外公一个人扛回家的。长年累月里,那些曾在外公肩头散发出松香的木板只有烟尘的苦味,木板的纹路也如同外公的脉搏一样模糊了。
今年是外公去世的第八个年头,清明时节,我格外想念外公。
万修琴,女,土家族,现就职于印江自治县文联,贵州省作协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贵州作家》《贵州日报》《铜仁日报》《梵净山》等,有作品入选《铜仁作家年度选本》(团结出版社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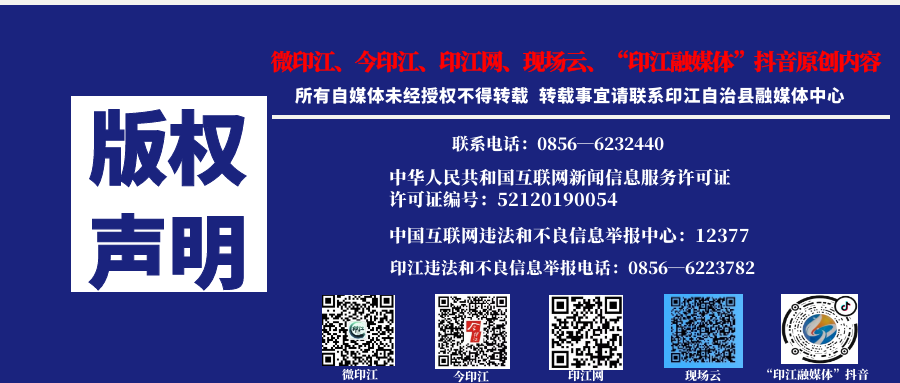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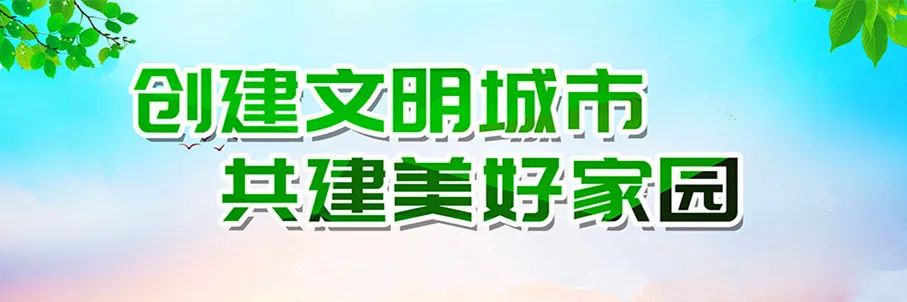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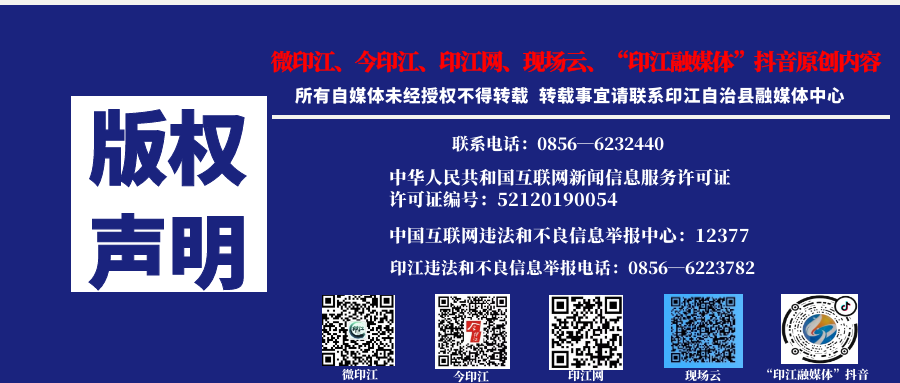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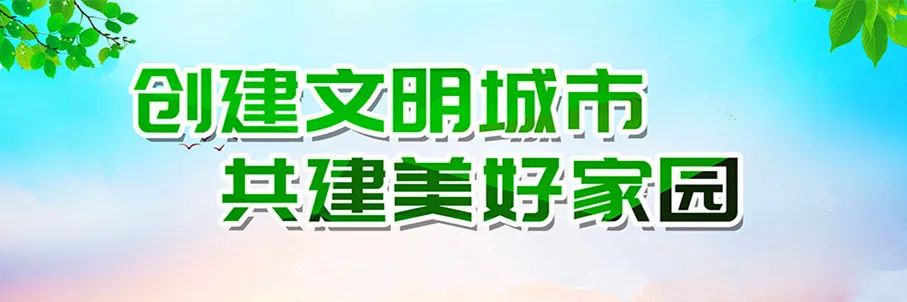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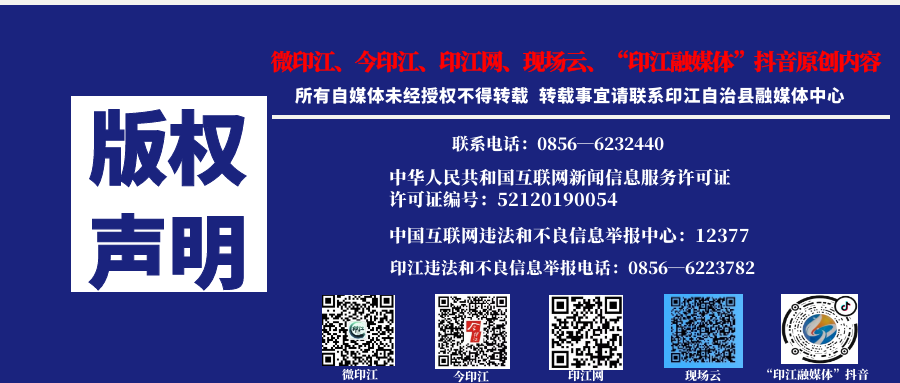 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
监制:左禹华 总编:蒋智江 编审:张江勇 编辑:王琴